导语: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紧迫性愈加凸显。近日,太和智库举办专题研讨会,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文汇报》资深驻法记者郑若麟先生结合他在法国“舌战群儒”的亲身体验和“执笔为戟”的工作经历指出,新时代,媒体宣传已经成为中西方模式博弈的竞技场,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为此,我们必须了解西方的游戏规则,讲究技巧方法,注重长期经营、布局累积,久久为功,唯此方能获得实效,让中国故事在新时代更加鲜活精彩,拨动西方和世界的心弦。现将其主要观点梳理成篇,以飱读者。

世界上有两个“西方”,一个是理论上的“西方”,一个是现实中的“西方”,两个“西方”的表现往往截然相反。理论上的“西方”,政治体制、制度设计、社会管理公平公正、自由开放,但现实中的“西方”,却幕后操作盛行,超出想象。
所谓的“公平公正”常为政治所操弄。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时,有一个官方正式确认的总统候选人叫舍米纳德,他在1995年就是总统候选人,而1995年我自认为跑遍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竞选集会,但令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当时居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根据法国的选举规定,每名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都应是一样的,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舍米纳德呢?我通过全面观察,终于发现了他们操作的手段和技巧。舍米纳德在电视上出现的时间长度的确与希拉克等其他总统候选人一样,但却往往被安排在很少有观众的播出时段,比如凌晨三四点,这样安排的结果就是没有多少选民了解他的观点,其得票率极低自是必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西方所谓的“公平公正”往往只存在于理论上,而实践中的“公平公正”往往会被“操作”掉。
我们耳熟能详的“言论自由”,在西方政治形态中其实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是由法律的有形框架和“政治正确主义”的无形枷锁严格限定的,框架和枷锁一旦确定,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卸任不久后因癌症病逝。翌日,一本名为《大秘密》(Le Grand Secret)的书问世,作者是密特朗的“御医”Claude Gulerg。他在书中透露,密特朗1981年首次当选总统的六个月后,即被查出患上了癌症。当时知晓此事的几名医生被告知这是“国家机密”,绝对不允许对外界透露一丝一毫。当时法国还有一本名为《病夫治国》的书,该书揭露了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向公众隐瞒癌症病情,最终死于任上,引起法国舆论的轩然大波。因此,密特朗竞选时便许下诺言,将每年公开一次他的健康报告。但如果信守承诺公布癌症诊断结果(当时医生认为密特朗只能活三个月至三年时间),密特朗的政治生涯将划上句号。于是总统的癌症成为“国家最高机密”,医生们在积极为密特朗治疗的同时,对外公布的却是“总统健康良好”的虚假报告。显然,这一隐瞒改变了法国的历史进程。密特朗不仅没有辞职,还继续了“病夫治国”的传奇,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患有癌症却成功连选连任的总统。《大秘密》一书是1996年1月17日运至书店的,我当天上午就去抢购了一本,可第二天这本书就被禁止发行了。除了已经卖出的四万册外,其他剩余全部被查封,理由是“医生无权向公众透露病人病情”。“该书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这一明显违反法国宪法出版自由规定的判决是由法国巴黎大法庭做出的。为此,作者与出版社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直到多年后欧洲人权法院裁定法国司法判决违反欧盟人权规定,这本书才得以解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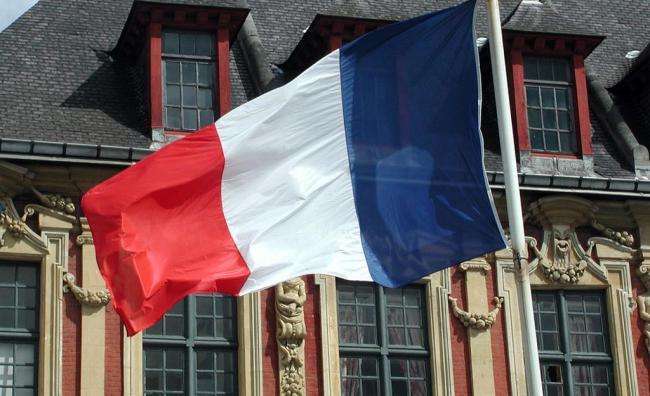
这一事例告诉我们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法国“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撒起谎来照样“脸不红、心不跳”,甚至堂而皇之。试想如果选民了解到密特朗已经身患癌症,还会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他吗?二是法国司法当局在必要时照样会以“法律的名义”禁止个人的言论自由。
我手头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法国著名记者Henri Alleg所著的《问题》(La Question)。我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朋友介绍与Henri Alleg见过面。当时我的朋友说,你不是想了解法国吗,我介绍你认识一位坐过牢的法国知识分子。《问题》一书是Henri Alleg在狱中写的,揭露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酷刑的秘密。其中有一段非常著名,Henri Alleg引用一名审讯他的军官的话写道:“你会开口的!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将开口!我们在印度支那打过仗,使我们有了认识你们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就是盖世太保!你知道盖世太保吗?”然后这名军官挖苦Henri Alleg说:“你写有关酷刑的文章,是吗?混蛋!好啊!现在就让你尝尝法国陆军第十伞兵师送给你的酷刑。”这本书一出版即被查封,一直到十几年以后才解禁。
因此,给西方人讲故事,千万别被其所谓的“自由客观、公平公正”给唬住。曾长期旅居法国的作家、《谁在导演世界》和《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作者边芹有这样一个观点:只有随意发生的事件,没有随意产生的新闻。这是一句应该列入我们新闻教学的至理之言。每一则新闻都会被当作某种工具,传递某种信息。既然是工具,那么必要的设计与安排是很自然的。我身在西方,二十多年近距离观察西方的媒体与舆论,对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深有体验。
在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权力架构并不是很重要。德国历经四个多月,近日才完成组阁谈判,新一届德国政府可能今年3月底才能成功组建,但德国社会照样运转。比利时曾经差不多一年没有政府,社会运行也没什么问题。这说明,西方国家的权力中心不是政府,而是一个比政府权力还要大的隐形集团。根据我在法国当记者十多年的观察研究,我发现法国真正的三权分立是财团、政府和媒体,其中财团的权力是最根本、最大的。在西方,如果财团出现问题,哪怕政府再强有力,社会也运转不下去。
西方国家的宣传职能主要由媒体、广告、电影承担,其背后无法摆脱财团的影响。西方财团控制的媒体非常自觉地把西方的体制说成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征服性特征的文明。只有把西方的体制说成是世界最好的体制,才能有征服他人的依据。所以西方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正确主义”限定着西方的媒体必须扮演“宣传西方体制至上”的角色。西方国家都有舆论风向标,法国有《世界报》和《解放报》,美国有《纽约时报》,这些报纸的报道就是一种政治定调。西方民众看中国发生什么事不是通过《人民日报》,而是通过西方的主流媒体,认为那些主流媒体的报道才是客观的。西方国家的广告发挥着强大的灌输功能,广告也都是由财团管控和操作的。财团做的广告,表面上看是宣传商品,但仔细分析,这些广告都在用同样的逻辑影响你,他们会暗示只要你买了他们的产品,你的生活就会得到根本改观,然后引导你去想,为什么会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那是因为西方的体制好、制度好。电影更是西方意识形态灌输的有力工具。西方政府资助拍摄的电影一定是有目的的,只不过常常冠以艺术片之名。比如法国文化部支持的戛纳电影节及其旗下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电影无一例外是表现中国负面形象的。看清这点,我们就应该明白西方所讲的故事是具有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的。

在西方,讲好西方故事的责任在于媒体、广告和电影,而在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中国的媒体宣传基本上不为西方所接受,中国的广告还未能很好地发挥对外宣传的作用,中国的电影亦未能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也就落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比谁的嗓门大、喇叭多。当人家不听你讲的时候,你的声音再大,他们也会把耳朵堵上。不要以为办几个外语电视台,甚至办到外国去,就能够夺得话语权,其实这只是在比嗓门大,是对话语权天大的误解。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通过西方的媒体,因为这才是西方公众信任的媒体。如果你去问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是否会看中国媒体的报道,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因为他们认定中国不是一个自由选举的体制,所有媒体都是官方主导的,所以会选择性拒绝接受。这种背景下,你在中国的媒体上喊破嗓子他们也不会去听去信,只有在西方的媒体上发声,他们才有可能去看去听。在话语权之争中,用好西方媒体会让我们事半功倍。
总之,与西方交往,不仅要和政府打好交道,还要与财团、媒体打好交道,这样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讲中国故事,如果只是一味直白地说中国体制如何好,中国人民如何友善,是绝对行不通的,相反还有可能被别人当成反面教材。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特殊背景下,要把中国的声音传播出去,就一定要找到突破口,讲求技巧方法。
我曾到法国电视台,同法国外交部人权国务秘书和绿党总统候选人辩论西藏问题,当时所有法国的舆论都认为中国军队镇压了藏人,显然我还没去就已经处于劣势,要把这个局面掰过来绝非易事,更何况对手是能言善辩的政治家,我处于“弱者”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向电视台提出,我是外国人,法语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一定要保证我讲话的时间,而且尽可能要求辩论双方不要打断对方的发言。我还专门预设了在发言时遭到对方打断时的回复。不出所料,辩论中,对方频频打断我的话。于是我适时抛出了我的回复说:“你们请我来,不是让我作为被告来听判决书的吧?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请不要打断我的话。”这句话效果非常之好,对电视观众震动非常大,观众会认为,即便你认为对方没理也不能打断他,更不能不准他讲话。法国观众虽然不一定完全赞成我的观点,但对一个“弱者”遭到无理对待还是非常反感的。因此,我作为“弱者”反而赢得了优势。一周后,该电视台又请我去。我觉得奇怪,因为一般法国电视台不会反复请同一位嘉宾。著名主持人Paul Amar告诉我,上一期节目播出后,电视台收到大量观众抗议,质问为什么请了一位中国人来,却不让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电视台不得不再次请我来发言。显然,我的举动博得了观众的同情,也让观众更加愿意聆听和相信我说的话。
同样是到法国电视台与法国人辩论西藏归属问题,我随身带去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在旧书摊上淘到的,是1826年一位著名的法国地理学家编写的《世界地图册》,其中一张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明西藏是中国的。我把这幅地图一打开,他们顿时傻眼,“西藏不是中国领土”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张地图的呈现,比讲十分钟的话更有说服力,因为在电视上,形象、画面更能说明一切,何况我用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石头”。
如果用文成公主的史实来说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方人是不认同的。因为在欧洲,各国皇室相互通婚是常有的事,不能说一个法国公主嫁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就成了法国的一部分。但我还是从法国的史料中找到了一个佐证,布列塔尼历史上并不属于法国,但当法国把公主嫁到布列塔尼后,布列塔尼就变成了法国的领地。这是布列塔尼独立主义者告诉我的,这个例子一举,一下戳到了法国人的痛处,他们顿时哑火。

中国的主持人在访谈前一般会把问题列好发给嘉宾,并事先给嘉宾打电话沟通。而在法国,电视台从来不事先把问题给你,但会给你打电话,目的是摸你的底。开始我不明白,一来电话我就跟他们谈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个问题怎么看。后来我才发现,等你到了电视台,问的问题跟电话里的根本不相关,而是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一套让你难堪的问题。法国电视台并不想让你表达你想表达的信息,而是想制造冲突、丑闻,看你出洋相。后来慢慢有经验了,他们再打电话,我就跟他们胡诌,等真正访谈时,绝不受他们的干扰,直陈自己的观点。与西方媒体打交道学会隐真示假很重要。
法国有一个常驻泰国的记者,以旅游者身份获得签证进入西藏,偷拍了一部片子,用来呼应达赖所谓的“西藏正在经历一场文化种族灭绝”的言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敏感的话题。我应邀就这个问题与这名记者、达赖集团驻法国代表以及法国国民议会极端反华的“西藏问题小组”主席进行电视辩论,加上立场明显偏袒达赖的主持人,我面临以一对四的不利局面(这也是我参加法国电视辩论的常态)。我心知肚明,法国那些所谓的“西藏问题专家”,其实都是一些对西藏并不了解的人。当那位记者发言抨击了一番中国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灭绝”这个词在西方非常敏感,因为它会使人联想到二战犹太人的命运。达赖集团确实找到了一个攻击中国的“好词”,只是它完全不符合事实)之后,我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天葬?”那位记者回答说:“我知道。”我从他的迟疑中看出来,其实他并不知道。于是我提高了一点声音再问:“你真的知道吗?”他犹豫了一下,轻声回答说:“知道啊。”这时我已经肯定他对天葬一无所知。于是我说:“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天葬?”他傻了,只好尴尬地承认不知道。于是我就当场解释什么是天葬。这时主持人拼命想打断我,因为尽管她也不知道什么是天葬,但从我的语气和在场达赖代表的脸色看,她意识到这肯定是一个不利于他们攻击中国的问题,因此她拉下文明礼貌的面子不让我说。我坚持在他们的打断声中说完,最后又总结道,大家都知道,天葬是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可能接受的做法,而中国连这种习俗都允许藏人保留下来,说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种族灭绝”岂不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主持人和达赖代表当时拼命地想打断我,阻止我说下去。但他们越是阻止,观众就越是好奇。最后,“天葬”这个法国人闻所未闻的词使他们对中国的污蔑不攻自破。
要想改变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我固有成见,绝非一场辩论、一部电影、一个广告、一本书就能做到。而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一个正面、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不是一次援助、一笔商业大单、一场国际会议、一届体育盛会就能办到的。这需要我们深耕细作,润物细无声地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才能水到渠成。
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创造更多机会让更多中国人在西方媒体上发声。驻法期间,我有时会在马路上被人拉住,他们会说,“我看过你的节目,我支持你。”可其实聊了几句后才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说过什么,只是因为经常看见我出现在电视上。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事实:只要中国人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良好起点。也许我所言并不能完全改变西方人的看法,但我在法国媒体上代表中国发声,至少会挤掉一个反华分子的出场机会,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成功了。我们要善于发现和培养这方面有潜质的中国留学生,鼓励和帮助他们进入西方媒体工作,帮助国内知名学者出版外文书,扩大他们在西方的影响力。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未来至少需要在每个西方国家培养几十位这样的人,让他们成为传播和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坚力量。

电视节目一经播出就过去了,但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讲清,为此,还要用好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体讲好中国故事。西方人喜欢阅读,纸质媒体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播途径,它承载的信息量多且可以流传,有辨别力的人会分析里面的内容,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比如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用法文发表,其中提到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共产党的人数,达到1亿人。《世界报》看到后派人核实,发现是真的,于是写了篇跟踪报道,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再比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世界”,很多法国人有疑问,因为法文的“和谐”有“把你变成我”的意思。如果直译极易引起法国人的误解。我迅即发表文章,说明“和谐”的意思是指“中国的外交是一个没有敌人的外交”。后来我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和中国人的真实现状,又用法语写了一本书叫《与你一样的中国人》,在法国出版后反响很大。
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热衷于在国外搞电视节目和创办电台,为此花了很多钱,虽然上报的统计数字非常漂亮,但从实际来看,受众寥寥,成效不彰。“今日俄罗斯”和“半岛”是两个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非西方媒体。“今日俄罗斯”是普京任命他的一个亲信组建的,并给予他莫大的权力,雇佣了很多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用西方人的思维和运作方式去做。“半岛”也一样,聘请了很多BBC的人去做。伊斯兰教、东正教与基督教同属一神教,因此,不管是“半岛”也好,“今日俄罗斯”也好,他们的运营者都非常了解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所以说,办好对外电视广播媒体,重要的不在于规模数量多大,关键是要学会从西方的逻辑思维出发讲好中国故事,采用合理恰当的方式搞好媒体的建设与运营。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并用他的所见所闻发表了大量报道,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客观地讲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故事、讲述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故事、讲述朴实善良的中国人民的故事、讲述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故事,在美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宣传不能只是我们自己说自己好,还要让别人真心实意地说我们好。要更好地利用社会和人文交流途径,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用事实和情感真诚地打动他们,让他们把一个真实、鲜活、正面的中国讲述给他们本国人民,讲述给全世界。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实际上是第一大经济体),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难得的战略契机。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寻求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因此,西方财团不希望跟中国彻底交恶,当然也就不会允许他们控制的政府和媒体无底线地抹黑中国。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没见过他们找俄罗斯人或者伊朗人到电视台为俄罗斯、伊朗辩护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他们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利益无关痛痒,但对中国却需要把握一个平衡。据统计,现在法国媒体上每天出现的中国新闻仅次于美国和中东。
过去,我们认为西方不了解我们,对西方外宣的主基调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没发展到你们那个阶段,还做不了你们现在做的事情”,主要目的是避免西方误解。但我们慢慢发现,其实西方国家很了解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国家制度的优缺点,但就是希望我们变成他们的样子,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控制我们。对于西方而言,控制一个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变成“民主选举制”国家,这样,他们就能运用所掌控的全球媒体非常娴熟地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操控。对此,法国著名学者伊格纳乔·拉莫内在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量身定制的民主》中说:“华盛顿一贯以‘非民主体制’来贬低其敌对国家,唯一能够逃脱这一诋毁的条件,就是‘自由选举’,而如果选出来的不是华盛顿所青睐的还是不行。只有选出一位亲美的人,才是民主。”
在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抵御西方颜色革命最有力的武器。随着中国迅速崛起,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告诉西方乃至世界,中国有中国的模式,这个模式最适合中国,不可替代,同时,这个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路径选择。模式是什么?模式就是竞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竞争。中国不向西方“输出”中国的模式,西方也不要指望向中国“输出”西方的模式。今天在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这场竞争中,谁胜谁负还未可知,但西方的衰落却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模式正在影响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比如很多非洲国家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的就是中国模式。”
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西方一向自诩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尽管面临种种问题,但他们始终认为没有比这种体制更好的了。正如丘吉尔所言,“资本主义是一个坏体制,但所有现行的其他体制都更加不行。”于西方而言,问题和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了一个可行的、与西方现行体制不同的替代模式。正因如此,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也更加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意义。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