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始,伊斯兰教即传入中国。1000多年以来,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并迅速成长,但并未完全融入中国主流文化。这在包容性极强的中国文化中是非常少见的。历史上,许多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以后,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中国人的宝贵思想资源。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就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体系中,与产生于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一起,对中国人的人格塑造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即使是封闭性极强的犹太教,也曾被中国社会逐步同化吸收,宋代聚集于开封的犹太教团就是如此。

两种文化要相互融合,必须都要具备开放性和宽容性。一方面,是外来文化要有融入本土文化的意愿;另一方面,是本土文化要有接纳外来文化的胸襟。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毋庸置疑,而对于伊斯兰文化的开放性,当今学者普遍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发展历程,发现它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曾不断向中国文化主动融合靠拢,体现出开放性的一面。
在伊斯兰教早期传入中国时,就有穆斯林学习儒家文化。唐宣宗时期,侨居中国的大食(阿拉伯)人李彦生熟读儒家经典,一举中第。虽然有人不同意录取一个“蕃客”,但也有很多官员认为他“行夷而心华”,因而最终被唐宣宗钦点为翰林学士。元代的维吾尔人廉希宪是当时的大儒许衡、姚枢等学者的弟子,笃好经史,被元世祖称之为“廉孟子”。蒙古族穆斯林康里部的不忽木与其他色目人坚童、太答、秃鲁等人一起向元世祖上书时称自己是“俾习儒学”。大书法家蒙古族穆斯林康里巎巎(nao,二声)也自称“儒者”,而且指出:“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云南设立行省后的首任行政长官平章政事,塔吉克人赡思丁,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不仅在云南修建了第一座拜祀孔子的文庙,而且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等著作传世。到了明清时期,许多伊斯兰学者更是通过吸收儒家文化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开始了理论上“以儒诠经”的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汉语撰写的著作,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天理命运说》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得到了当时主流文化界的认可和赞赏,也加深了伊斯兰信众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从而推进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进程。这些穆斯林学者的思想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儒道释经,主动融合中华文化。明清之际的穆斯林学者担当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化交流学习的桥梁角色,正如刘智在《天方典礼》所说:“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例如,在宇宙起源方面,王岱舆吸收、改造宋明理学中的“无极”“太极”和“一”学说,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等概念。刘智则在“无极”“道”“太极”作为物质世界总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无称”这一概念,作为先天世界的总源。在社会伦理方面,刘智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五典”说来丰富伊斯兰教法,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方面的人伦关系。马注把儒家的“明明德”的说法,与伊斯兰教的“伊玛尼”(即“信仰”“信德”之意)说衔接起来,认为“明明德”就是“培养伊玛尼”。诸如此类以儒家道家经典思想诠释伊斯兰教教理教义,使得伊斯兰文化融入大中华民族文化具备了可能性。

二、正确处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相互交融,将对真主的崇拜与对国家的忠诚联系起来。王岱舆在《正教真诊·听命》中就指出,如果只知道信教而对国家无所贡献,则人生也不算完整:“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事亦不足为功。”明清四大伊斯兰汉文译著家之一的马德新在遗嘱中说道:“在中国国位为先,教位次之,先复国而后复教。国正天心顺,教正国安宁。凡我后生,须忠于国,勤于教,恪固诚一。”他正确地定位了国家和宗教之间先后顺序,并指出“教正”对于国家安宁的重要性,将爱国与爱教进行了有机统一。这些伊斯兰学者调和了国家与宗教二者之间的矛盾,为教育和引导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树立了良好榜样。
三、合理协调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在明清时期“以儒诠经”的过程中,伊斯兰学者按照中国“政主教从”的文化传统,来处理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律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教法的功能因此有所变化,即由处理穆斯林内部诉讼的通制,变成了约束穆斯林行为的礼法。明清时期的汉译伊斯兰著作,就多以“礼法”一词来指称伊斯兰教法。例如,马复初在《礼法启爱》中所谓的“礼法”,都是伊斯兰教法的内容,涵盖了沐浴、礼拜、婚姻等;刘智的《天方典礼》中,在论述伊斯兰教法时,也将其限定在伊斯兰宗教礼仪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此,中国伊斯兰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伊斯兰的传统,即穆斯林在公共政治生活中遵从世俗社会的法律,伊斯兰教法则局限于私人领域和宗教领域。
“阐旧教以辅新政”,以上对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伊斯兰学者的观点的简要概述,对于我们今天对待伊斯兰问题都有重要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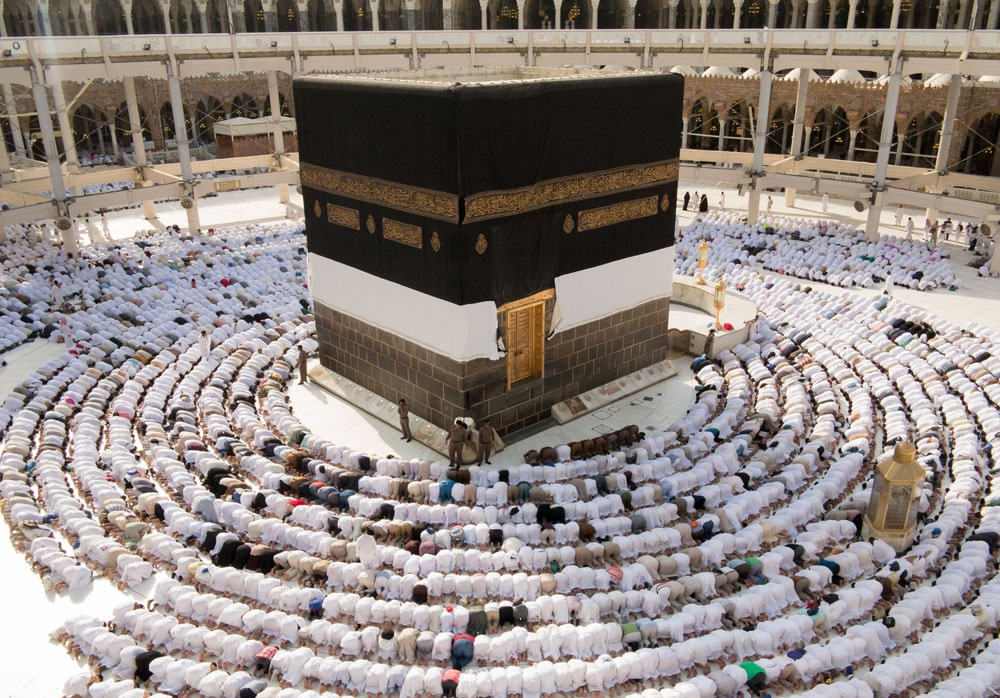
一、中国伊斯兰文化必须本土化,可借鉴儒家、佛家、道家等经验,建立中国伊斯兰文化道统。经过明清两代伊斯兰学者的努力,已经建构起了一整套用儒、释、道概念诠释伊斯兰教理教义的话语体系。例如,马注以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来论证儒家和伊斯兰是“教异而理同”;刘智在《天方典礼》中以佛家的“性海”“灵根”以及道家的“动静”“玄机”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宇宙观。既然儒家、佛教或者道教的术语概念可以用来阐释伊斯兰教法,则我们也可以仿效历代政府对于儒家、佛教或者道教树立道统的管理经验,将历史上那些既具有伊斯兰深厚学养又具有大中华文化认同理念的学者,如廉希宪、不忽木、赡思丁、陈思、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树立为中国伊斯兰圣贤的典范,建立起中国本土伊斯兰文化的道统,并使之得到广大穆斯林的认可,最终建立起有别于伊斯兰教的中国伊斯兰教。
二、在学术研究上,要扶持并加强对伊斯兰道统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凸显其与国家主流文化思想相一致的方面。历史上,中华主流文化倡导中庸、多元、合作、和平,反对极端、分裂、对抗、暴力。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中国伊斯兰,由于伊斯兰先贤的积极倡导,也逐渐接受了这些观念,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并与中华各民族和谐相处,以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教。要积极引导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对中国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先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国家应在课题设置、研究资助等方面,大力加以扶持,鼓励学者为伊斯兰的中国化与世俗化提供理论基础。

三、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阐旧教以辅新政”。中国历史上的伊斯兰学者在阐释伊斯兰教理教义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向儒、释、道等当时的主流文化学习借鉴,因而中国本土化特色非常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避免文化冲突的作用。今天,我们应该积极鼓励伊斯兰教信众发掘、继承和弘扬伊斯兰先贤的进步观念,延续历史上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主流文化对话的互通传统,巩固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成果。我们更应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伊斯兰教法的自我革新,深入挖掘其中有利于国家安定、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积极成分,用当代主流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促进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等积极适应,引导穆斯林正确处理好政教关系以及宗教文化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来。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